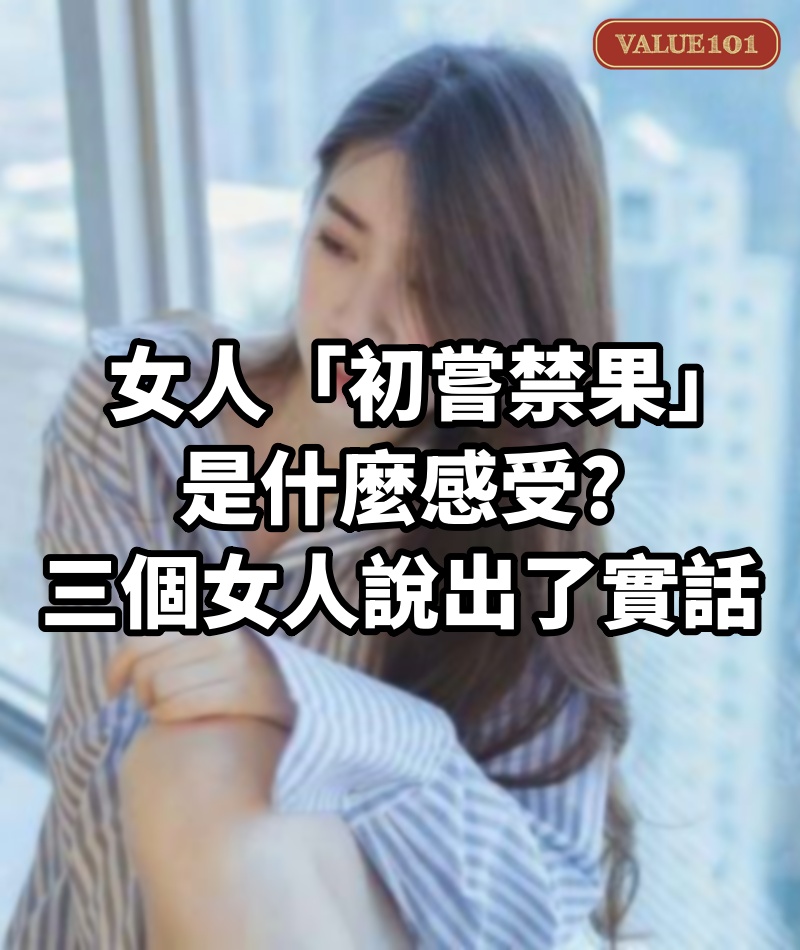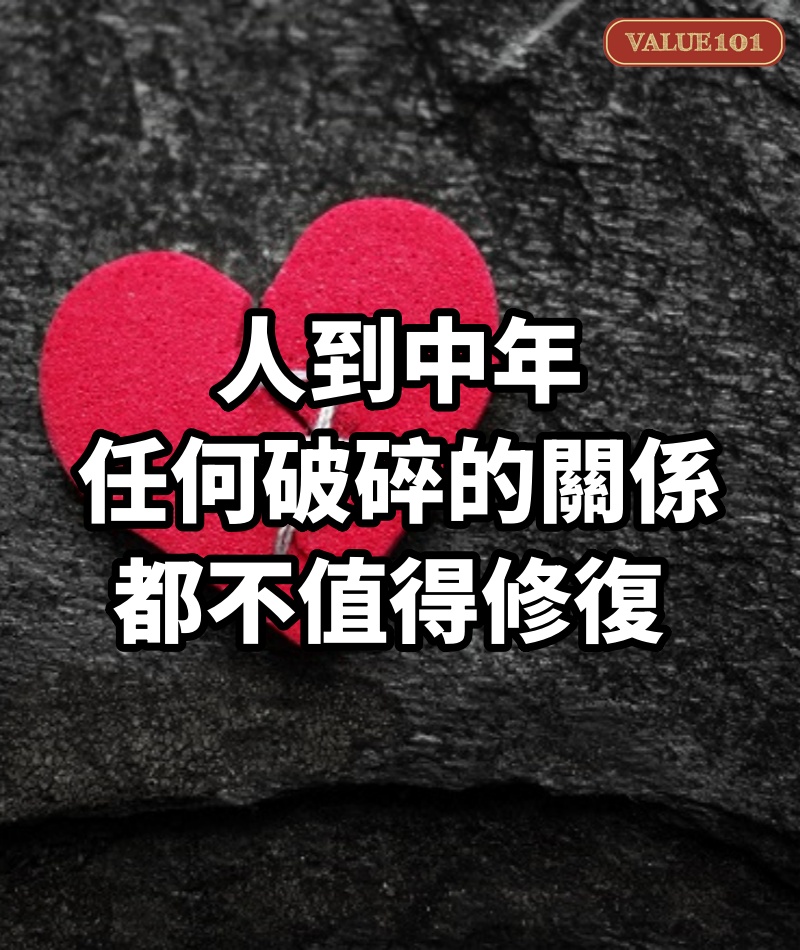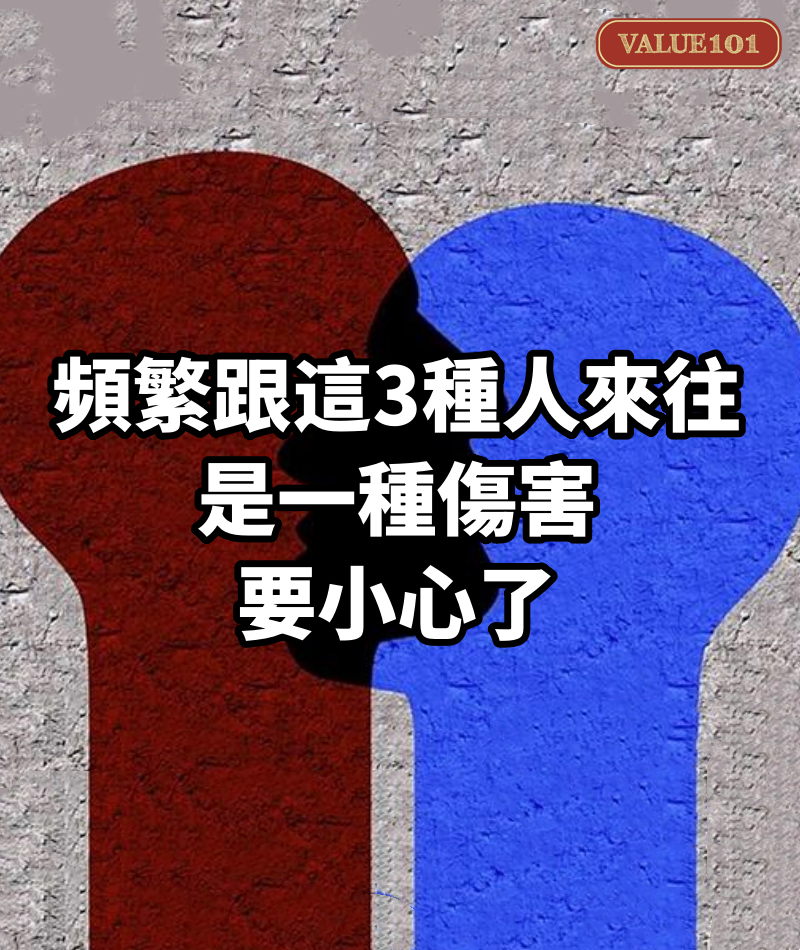梁實秋:那些會說話的人,人生已經贏了一大半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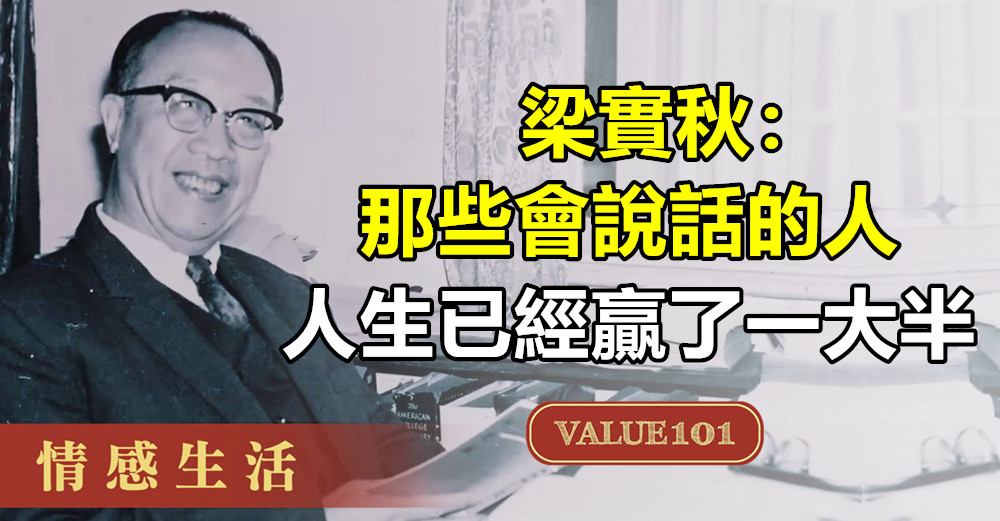
要問民國時期哪位作家特別詼諧幽默、能言善辯,那一定非梁實秋 莫屬。
他能把一個“懶”字說得“理所當然”:
“可以推給別人做的事,何必自己做?可以拖到明天的事,何必今天做?”
他吐槽邋遢男人,在七分犀利中帶著三分幽默:
“西裝褲儘管挺直,而耳後脖根土壤肥沃,常常易於種麥。”
在梁實秋的散文中,他常常用這樣輕鬆詼諧的風格,寫盡世間的千姿百態。
《好好說話,好好生活》 就是一本收錄他寫的關於說話技巧和處世之道的散文集。
在書中,他談人情世故、談生活感悟,時而風趣幽默,時而嬉笑怒罵。
其中最引人深思的,是他對“好好說話”的深刻註解:
“好的語言就像明媚的笑容,擁有直達人心的力量。好好說話的人,運氣都不會太差。”
是啊,如果說話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能,那好好說話,就是一個人後天習得的修養。
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:
“智者說話,是因為他們有話要說;愚者說話,則是因為他們想說。”
話,人人會說,但能不能把話說好,卻最能看出一個人處事的能力和情商的高低。
有些話,最好不說;有些話,盡量少說;
有些話,則需要幽默地說。
仔細觀察就能發現,那些懂得好好說話的人,往往一開口,就已經贏了一大半。
在《好好說話,好好生活》一書中,梁實秋提到一件讓他啼笑皆非的事。
他看到一篇名為《文學作家中的胖子》的文章中,作者用非常戲謔的口吻寫自己偏胖的體態:
北大教授梁實秋先生像個“老闆”,教書神氣像,划拳神氣更像。
穿的衣服本來和別人用的材料差不多,到他身上好像就光亮不同,
說的話本來和別人是同一問題,到他口上好像就意義不同。
這段描述,讓梁實秋著實尷尬,他在書中寫下了自己當時的感受:
“近於胖,則俗,近於廋,則雅。
一個文人、一個作家,總宜於廋,一胖起來就覺得不稱,就大可以加以檢舉引為談資。”
他忍不住慍怒地回懟作者:
“俗而胖,與俗而瘦,我寧願俗而胖,不願俗而瘦,因為反正都是俗,與其外表風雅而內心俗陋,還不如里外如一的俗!”
這位作者為什麼一句話就能讓梁實秋感到特別不舒服?
其實就在於他用這樣帶著嘲諷的語氣去描述別人的體型,本身是不太禮貌的。
胖瘦只是一個人的外形,跟才華、能力都毫無關係,單拿來大肆渲染,往往就容易變成說人是非。
但顯然這位作者並沒有察覺到自己的不妥,所以他在文章中洋洋灑灑寫了一大段,還自我感覺良好。
我們常說,說話的藝術,就是語言的溫度。不會說話的本質,其實是不會做人,太過自我,只顧說得痛快,而忽略了被說的人有何感受。
生活中,也總有一些人熱衷於論人是非、說人長短。
看見人家夫妻和睦,他會“善意”提醒妻子:
“你老公最近都很晚回家,你要留個心眼才好!”
看到人家孩子琴棋書畫樣樣精通,他會酸溜溜地來一句:
“學這麼多東西,還不都是錢堆出來的!”
這些人總愛在生活中逞口舌之快,卻不知道自己脫口而出的一句話,很可能會給別人製造許多事端,也給自己帶來無盡的麻煩。
詩人本·瓊森說:“語言最能暴露一個人,只要你說話,我就能了解你。”
確實,一個人最愛說什麼話,他大致也就是怎樣的人。
說話知道輕重緩急,是一種認知能力,也是一份智慧。
說話懂得考慮別人的感受,是一種修養,更是一種善良。
所以,議人是非的“醜”話,最好不說。
不要讓一時的暢快,讓自己顯得缺乏素養。
更不要因為自己的口無遮攔,讓別人看透你的淺薄。
關於生活中的“廢話文學”,梁實秋在《好好說話,好好生活》中有一段讓人忍俊不禁的描述:
“嘗有客過訪,我打開門,他第一句話便是:'您沒有出門?'
我如果出門,現在如何能為你啟門?那豈非是活見鬼?”
對生活中的“廢話大師”,梁實秋則在七分吐槽中帶著三分詼諧:
“他們可以把人家的私事當作座談的資料,某人資產若干,月入多少,某人芳齡幾何,美容幾次,某人帷薄不修,某人似有外遇……說得津津有味,實則有傷口業的廢話而已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