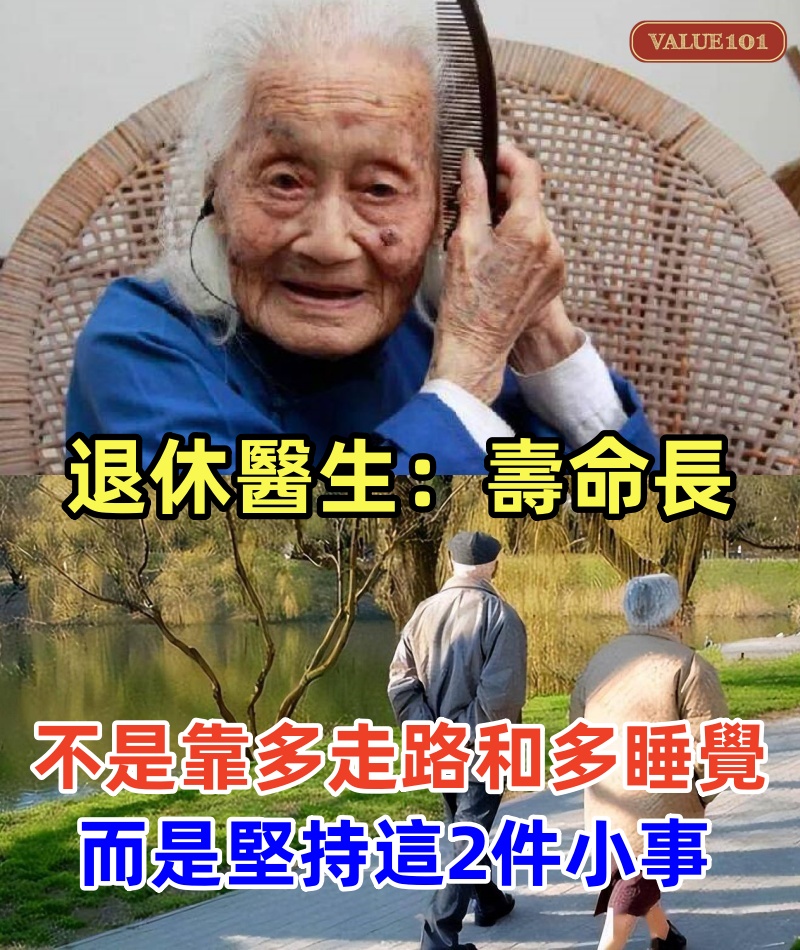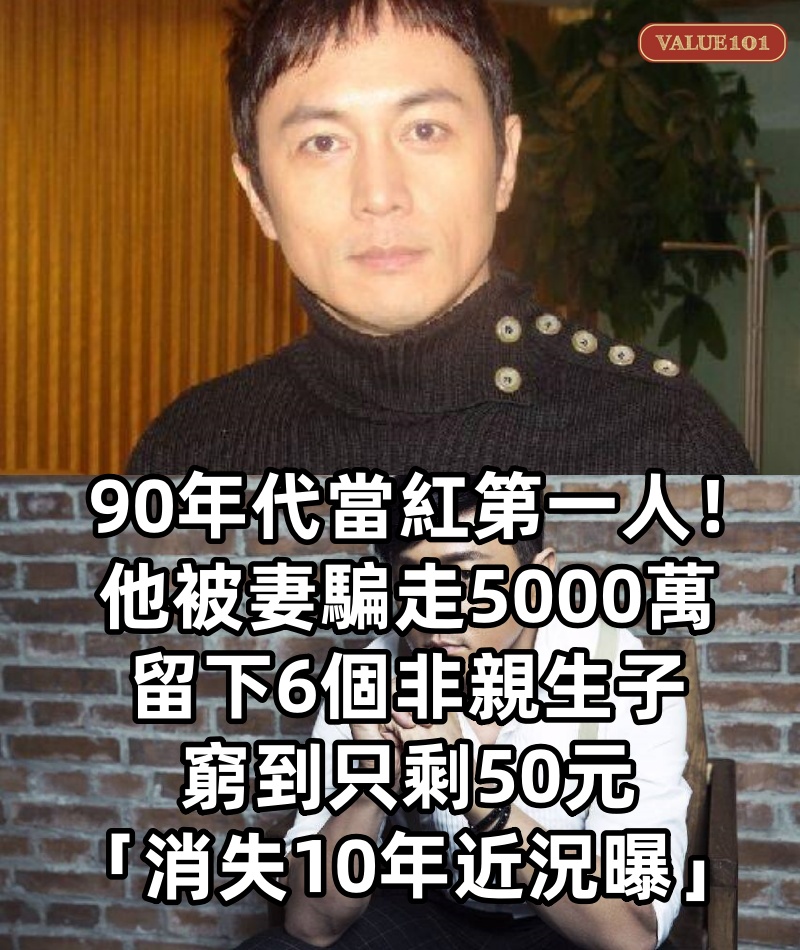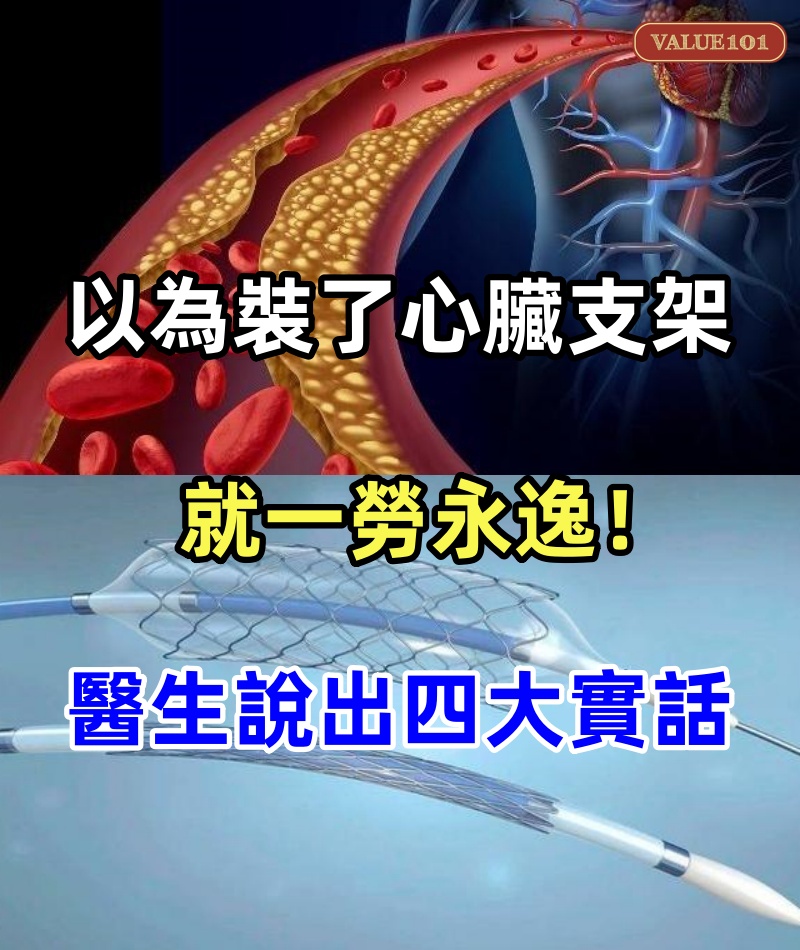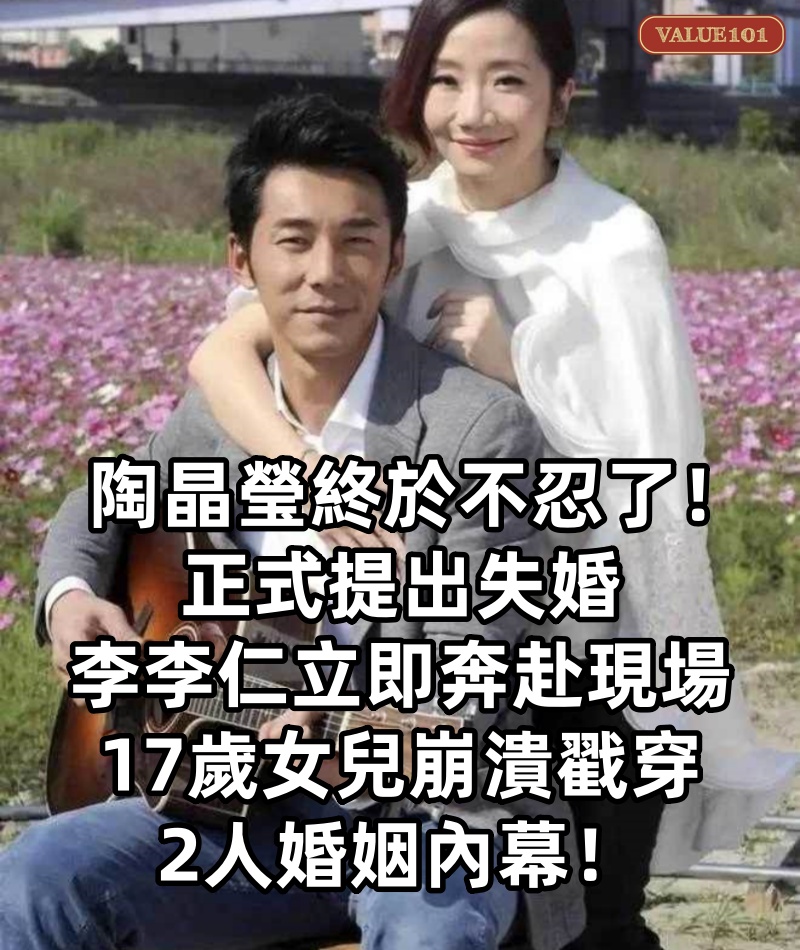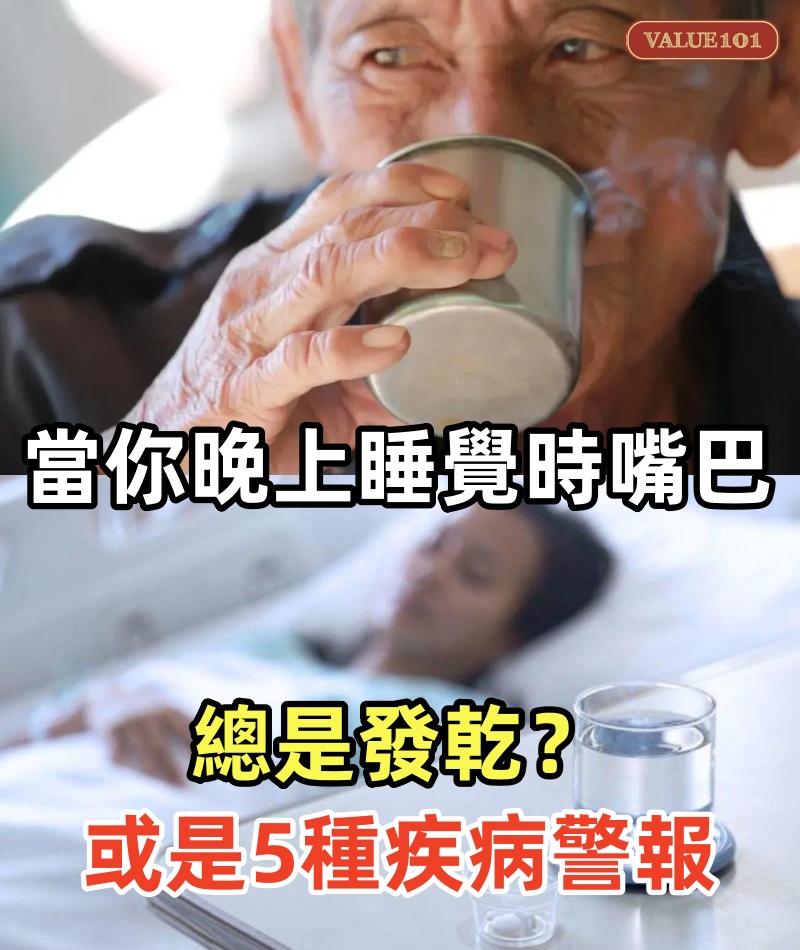懷孕32周被婆婆轟出門,8天後問我知錯沒,我:孩子沒了,離婚吧

那眼神讓周明莫名地感到一陣心悸,後面責備的話卡在了喉嚨里。
「醫生怎麼說?
孩子沒事吧?」他生硬地轉換了話題,語氣緩和了一些,走到床邊。
林婉沒有回答,只是閉上了眼睛,拒絕看他,拒絕和他交流。
周明有些尷尬地站在原地,看了看旁邊臉色不虞的鄰居阿姨。
「謝謝你送她來醫院,費用我之後轉給你。
這裡我來照顧就行。
」他試圖拿出男主人的姿態。
鄰居阿姨看了看病床上彷彿失去生氣的林婉,嘆了口氣,沒說什麼,留下了聯繫方式便離開了。
病房裡只剩下他們兩人,以及儀器規律的滴答聲。
周明在床邊坐下,沉默了半晌,才幹巴巴地開口:「媽……媽她就是那樣的人,刀子嘴豆腐心,你別往心裡去。
等孩子生了就好了……」
又是這一套。
林婉依舊閉著眼,但開口了,聲音沙啞而平靜,像在陳述一個與己無關的事實:「周明,我差點流產。
因為你媽推我,因為你沒有阻止。
」
周明身體一僵,臉上閃過一絲慌亂:「我……我當時沒反應過來……媽她也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「你出去。
」林婉打斷他,聲音依舊平靜,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決絕,「我不想看見你。
」
「婉婉……」
「出去!」她猛地睜開眼,看向他,那眼神里的恨意和冰冷讓周明瞬間噤聲。
他張了張嘴,最終什麼也沒說,站起身,有些狼狽地離開了病房。
門關上的那一刻,林婉的眼淚才無聲地再次滑落。
為死去的愛情,為可笑的婚姻,也為腹中命運未卜的孩子。
章節四:失去與決斷
接下來的幾天,林婉獨自一人在醫院保胎。
周明每天會來一次,有時帶著煲好的湯,有時只是呆坐一會兒。
林婉大多數時候閉目不語,偶爾開口,也只是必要的交流,冷淡得像對待陌生人。
王蘭一次都沒有出現過。
彷彿那天晚上歇斯底里將孕婦推搡至見紅的人不是她。
周明解釋說母親在家「反省」,覺得沒臉來見她。
林婉心中只有冷笑。
蘇晴請了假,天天來陪她,給她帶來換洗衣物和日常用品,幫她擦身,陪她說話。
友情成了她在這段至暗時刻里,唯一的光和溫暖。
醫生每天來查房,神色始終凝重。
儘管用了最好的葯,林婉的宮縮還是時好時壞,胎心監測的數據一直不理想。
胎盤早剝的情況似乎在緩慢加重,胎兒在宮內有些缺氧。
「林女士,您要有心理準備。
」第五天,醫生委婉地告訴她,「孩子的情況不太樂觀,才32周,如果……生存幾率會受影響,即使保住,也可能會有後遺症。
」
林婉的手緊緊抓住床單,指甲掐進掌心。
她努力吃著所有有營養的東西,強迫自己睡覺,保持心態平穩,盡一切努力想要保住孩子。

這是她的骨肉,是她唯一的希望了。
她甚至開始卑微地想,只要孩子能保住,其他的,她都可以不在乎。
第七天夜裡,她突然從睡夢中驚醒。
腹部傳來一陣前所未有、撕裂般的劇痛,下面的床單瞬間被溫熱的液體浸透。
不是之前的少量見紅,而是大出血!
她驚恐地按響了呼叫鈴。
值班醫生和護士迅速衝進來,一看情況,立刻臉色大變。
「快!準備手術室!急性大面積胎盤早剝!大人大出血!胎兒嚴重窘迫!」醫生急促地下達指令。
病床被飛快地推向手術室,走廊的頂燈飛速掠過,晃得林婉睜不開眼。
劇痛和失血讓她意識開始模糊。
她只知道,她的孩子,很危險。
她拚命地在心裡祈禱:「寶寶,堅持住,媽媽求你,堅持住……」
手術室的門砰地關上。
刺眼的無影燈打開。
麻醉醫生準備全麻。
失去意識的前一秒,林婉彷彿聽到遙遠的地方傳來胎心監測儀拉長刺耳的警報聲……
那聲音,成了她之後很多個夜晚的夢魘。
不知道過了多久,她在一片虛無中慢慢恢復意識。
首先感覺到的是腹部空蕩蕩的劇痛,和渾身插滿管子的不適感。
她艱難地睜開沉重的眼皮,看到的是蘇晴哭得紅腫的雙眼,和醫院蒼白的天花板。
「婉婉……你醒了……」蘇晴的聲音哽咽著,緊緊握住她的手。
林婉張了張嘴,喉嚨乾澀得發不出聲音。
她的目光下意識地向下,看向自己的腹部。
那裡……平坦了。
之前高高隆起的、承載著她所有希望和愛的地方,此刻被厚厚的紗布包裹著,只剩下虛無的疼痛。
孩子呢?
她的孩子呢?
她用盡全身力氣,看向蘇晴,眼神里充滿了 desperate 的詢問。
蘇晴的眼淚瞬間涌了出來,她別開頭,不忍看她。
主治醫生走了過來,面色沉重而疲憊:「林女士,您醒了。
很抱歉……我們儘力了。
急性胎盤早剝太嚴重,引發了大出血和子宮收縮乏力,為了保住您的生命,我們不得不進行了剖宮取胎術和子宮次全切……孩子……因為嚴重缺氧和時間太久,沒能搶救過來……是個男孩……請您節哀……」
男孩……
她婆婆心心念念的孫子……
沒能搶救過來……
子宮切除……
每一個字,都像一顆子彈,精準地射入林婉的心臟,將她打得千瘡百孔,血肉模糊。
世界失去了所有的聲音和顏色。
她感覺不到眼淚,感覺不到悲傷,甚至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。
巨大的、滅頂的空白吞噬了她。
她只是睜著眼睛,看著天花板,一動不動,像一具被抽空了靈魂的軀殼。
蘇晴在一旁捂著嘴,泣不成聲。
周明和王蘭不知何時也來了,站在病房門口。
王蘭聽到醫生的話,臉色瞬間慘白,嘴唇哆嗦著,似乎想說什麼,卻發不出任何聲音。
周明則一臉震驚和茫然,彷彿無法消化這個噩耗。
林婉的目光緩緩地、機械地轉向他們。
看到王蘭那張瞬間失去所有氣焰、只剩下驚恐和難以置信的臉。
看到周明那副彷彿天塌下來的無措模樣。
她的眼神里,沒有恨,沒有怨,沒有痛苦。
什麼都沒有。
只有一片死寂的、望不到底的虛無和冰冷。
那種冰冷,比任何歇斯底里的哭喊都讓人恐懼。
王蘭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,不敢與她對視。
第八天下午。
林婉依舊沉默地躺在病床上,像一尊沒有生命的雕塑。
蘇晴寸步不離地守著她。

她的手機響了,是周明打來的。
蘇晴看了一眼林婉,走到窗邊接起。
電話那頭,周明的聲音帶著疲憊和一絲小心翼翼:「蘇晴,婉婉……她怎麼樣了?
我媽……她想跟婉婉說句話……」
蘇晴強壓著怒火:「你們還有臉打電話?!」
「我們……我們就是想知道她好點沒……」周明的聲音底氣不足。
過了一會兒,蘇晴拿著手機,猶豫地走到床邊,低聲對林婉說:「婉婉……是……是你婆婆的電話……她說……想問你……知錯了沒……」
說出這句話,蘇晴都覺得無比荒謬和憤怒!
電話那頭,王蘭的聲音隱約傳過來,帶著一種故作鎮定、甚至試圖拿回主導權的施捨般的語氣:「……婉婉啊……媽知道你這幾天不好受……也知道錯了沒?
知道錯了就好好跟周明過日子,養好身體,以後……」
「孩子沒了。
」
林婉突然開口了,聲音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,像在陳述一個與己無關的事實,直接打斷了王蘭的話。
電話那頭瞬間死寂。
幾秒鐘后,王蘭尖銳失措的聲音傳來:「什……什麼?
你說什麼沒了?!」
林婉的目光空洞地望著前方,一字一句,清晰冰冷:
「你們周家心心念念的孫子,沒了。
」
「離婚吧。
」
章節五:永別與新生
電話那頭像是被瞬間掐斷了喉嚨,死一般的寂靜持續了足足十幾秒。
然後,傳來王蘭近乎癲狂、語無倫次的尖叫和哭嚎:「不可能!你騙我!我的孫子!我的大孫子怎麼會沒了?!是你!一定是你沒保護好他!你這個喪門星!賠錢貨!你還我孫子!!」
聲音扭曲刺耳,充滿了絕望和瘋狂的指責。
緊接著是周明慌亂的聲音:「媽!媽你冷靜點!婉婉?
婉婉你說的是真的嗎?
孩子真的……」
他的聲音也在顫抖,帶著難以置信的恐慌。
林婉沒有再聽下去。
她示意蘇晴掛斷了電話。
所有的喧囂、指責、哭嚎,都被隔絕在了另一個世界。
與她無關了。
蘇晴紅著眼眶,緊緊握住她冰涼的手:「婉婉,你想哭就哭出來,別憋著……」
林婉緩緩搖了搖頭,眼神依舊空洞,卻多了一絲極淡的、冰冷的決絕。
「沒什麼可哭的。
為不值得的人流淚,是浪費。
」
第二天,周明和王蘭跌跌撞撞地衝進了病房。
王蘭一夜之間像老了十歲,頭髮凌亂,眼睛紅腫,撲到病床前就想撕打林婉:「你還我孫子!你把我的孫子還給我!」
她被周明死死拉住。
周明看著病床上臉色蒼白如紙、眼神冰冷的林婉,又看著情緒失控的母親,臉上是前所未有的憔悴和混亂。
「婉婉……媽她受不了刺激……這到底是怎麼回事?
醫生不是說保胎嗎?
怎麼會……」他語無倫次,似乎還存著一絲僥倖。
主治醫生被護士叫來,冷靜甚至帶著一絲鄙夷地再次陳述了病情和手術情況。
「病人急性胎盤早剝,大出血,能保住命已經是萬幸。
至於原因,」醫生目光銳利地掃過王蘭和周明,「情緒極度激動、腹部遭受外力撞擊、以及後續沒有得到及時的舒緩和照顧,都是重要誘因。
你們作為家屬,難道不清楚嗎?」
王蘭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氣,癱坐在地上,開始嚎啕大哭,嘴裡反覆念叨著「我的孫子」。
周明臉色慘白,踉蹌著後退一步,靠在牆上,失魂落魄。
真相像一記重鎚,狠狠砸碎了他最後一絲幻想。
他看向林婉,嘴唇哆嗦著,似乎想道歉,想解釋。
但林婉先開口了,她的聲音不大,卻像冰渣一樣,冷硬刺骨:「周明,離婚協議我會讓律師送給你。
我什麼都不要,也什麼都不要你們的。
我只要求儘快離婚。
」
她的目光掃過癱在地上的王蘭,沒有任何情緒。
「帶著你媽,出去。
別再出現在我面前。
」
決絕,乾脆,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。
周明看著眼前這個陌生的妻子,她眼裡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溫柔和依戀,只剩下徹底的冰冷和厭惡。
他知道,一切都無法挽回了。
他的沉默和懦弱,他母親的跋扈和惡毒,最終徹底摧毀了他的家庭,殺死了他的孩子,也永遠失去了妻子。
他失魂落魄地扶起幾乎癱軟的母親,像兩條喪家之犬,狼狽地離開了病房。
從那以後,他們真的沒有再出現。
一個月後,林婉出院了。
身體上的傷口在慢慢癒合,但心裡的洞,或許永遠也無法填補。
蘇晴接她回了自己家,細心照料。
周明試圖通過電話、簡訊聯繫她,表達懺悔和彌補的意願,甚至同意離婚,但希望見面談。
林婉一條都沒有回,直接拉黑了他所有的聯繫方式。
所有事宜,均通過委託的律師處理。
離婚協議辦得異常順利。
林婉果然如她所說,凈身出戶,沒有要周家一分一毫。
她只想徹底斬斷與那個家庭的一切關聯,越快越好。
拿到離婚證的那天,陽光很好。
林婉站在民政局門口,看著手裡那本暗紅色的證件,感覺像是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鎖。
沒有想象中的解脫和快樂,只有一種劫後餘生的疲憊和空曠。
蘇晴擔心地看著她。
林婉抬起頭,迎著陽光,微微眯起眼睛。
蒼白的臉上,許久以來第一次有了一絲淡淡的、屬於活人的氣息。
「晴晴,」她輕聲說,聲音依舊有些沙啞,「陪我去個地方吧。
」
蘇晴點點頭:「好,去哪都行。
」
林婉去了一家花店,買了一束小小的、白色的雛菊。
然後,她讓蘇晴開車,去了郊外的公墓。
在一個安靜的、小小的墓碑前,她停下了腳步。
墓碑上沒有名字,只有一行簡單的日期——那是她孩子本該出生的日期。
下面刻著一行小字:「願你來去如風,永駐星空。
」
這是她唯一為孩子留下的東西。
用她僅剩的、全部的母愛。
她將雛菊輕輕放在墓碑前,伸出手,指尖冰涼的觸摸著那冰冷的石碑。
她沒有哭,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,站了很久很久。
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來,在她身上投下斑駁的光影。
風吹起她的髮絲,帶著初冬的涼意。
許久,她緩緩轉過身,看向身後一直默默陪伴的蘇晴。
臉上帶著一種洗凈鉛華后的平靜和堅韌,雖然脆弱,卻不再輕易破碎。
「走吧。
」她說。
聲音很輕,卻帶著一種重新開始的力量。
蘇晴上前,挽住她的手臂,給予她無聲的支持。
兩個身影慢慢走下台階,消失在公墓蜿蜒的小路盡頭。
陽光依舊溫暖,天空湛藍。
生活給予了她最沉重的一擊,幾乎將她徹底摧毀。
但她從廢墟中站起來了,帶著永久的傷痕和無法彌補的缺失。
未來的路還很長,或許依舊艱難。
但至少,她離開了冰窟,重新走在了陽光下。
為自己而活。